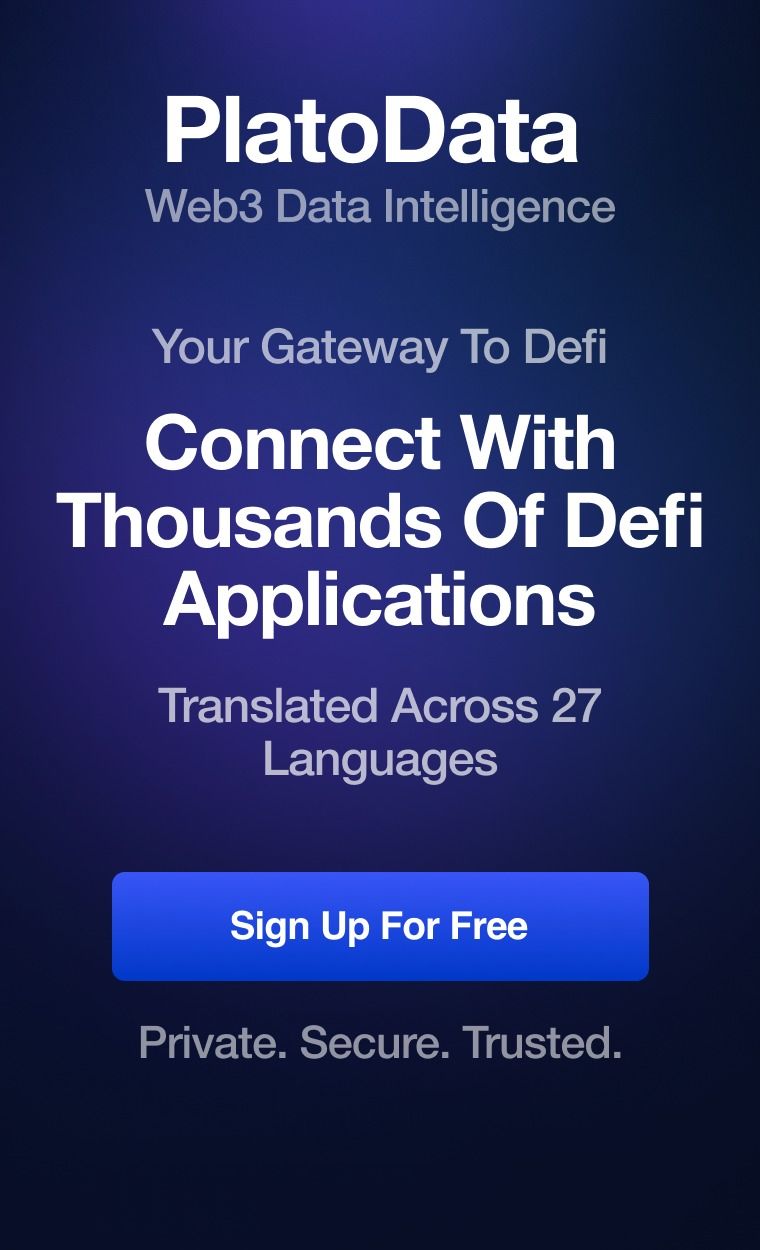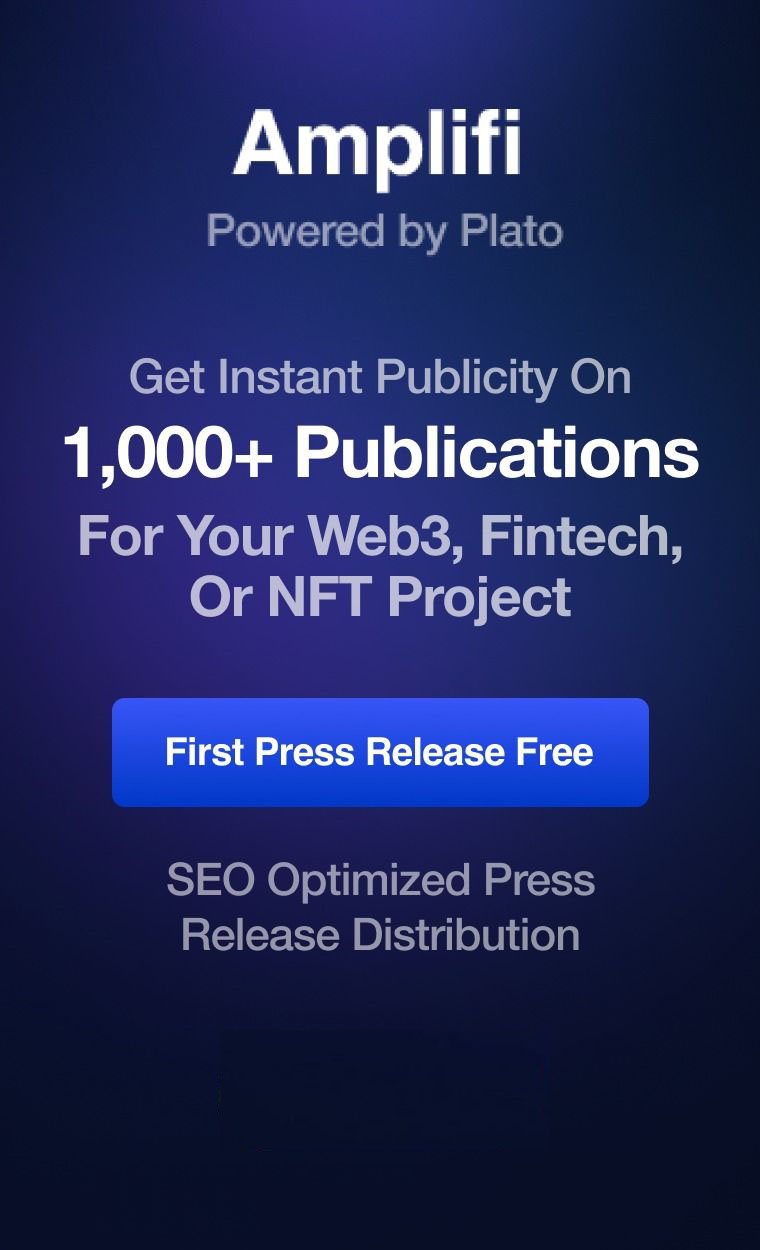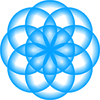编者注:Amanda Watson 于 2015 年加入 Oculus VR,并在达拉斯 John Carmack 办公室外的一个小隔间里工作,负责移动 SDK 工作到深夜。后来在加利福尼亚州,她从事 Oculus Link 和 Air Link 的工作,然后于 2022 年离开 Oculus。2024 年初,Watson 发布了 CitraVR 在Github上。这封信是为了“我从未向卡内基梅隆大学发出的道歉”而写的,原因是她 2014 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最后一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致相关人士,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有点晚了。我因拖延事情而臭名昭著(正如你现在可能知道的那样),但我仍然觉得有必要发送这张便条。我告诉大学我愿意向他们道歉 任何人 我们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伤害,而我完全有意这么做。我希望时间(如果有的话)有助于为我的笔记提供背景信息。
我实际上并不了解这封信所针对的受影响各方,因此我将介绍我的基础并准确概述这封道歉信的内容。去年秋天,我和一位朋友在技术机会会议 (TOC) 的一个空展位前呆了一段时间。我们收集了学生的简历,管理人员担心我们可能被误认为是该展位公司的招聘人员。随后我们注意到,虽然我们的本意可能是好的,但这给参加招聘会的学生以及负责组织活动的工作人员带来了麻烦。这是我们从未有意为之的事情,而且我们当然会对造成的事情感到非常抱歉。
我现在明白,行动和意图并不像所发生的事情的印象、反应和后果那么重要。也就是说,只要我在这里,我想你们中的一些人就不会介意听听我记得的完整故事。不是为了原谅我的行为,而是为了让我深入了解我和朋友的动机,以及为什么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真正的抱歉。
事发当天早上,我在 TOC 开业前 20 分钟到达了现场。通常情况下,我不会这么努力,老实说,穿着西装的尝试者在科技文化中给人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但我还是愿意冒这个险,因为我最想在 Oculus VR 工作。作为一名拥有高性能图形和系统设计背景的计算机科学和戏剧专业的学生,我没有很多明显的职业道路。去年春天,我听了 Oculus 研究员 Michael Abrash 的演讲,当他解释他们正在寻找的工程师类型时,我听到他描述了我。对我来说,Oculus VR 似乎是我验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并最终推动新技术诞生的一次尝试。
另外,说实话,我在常规求职过程中表现不佳。过去几年我收到实习机会的地方现在在面试的最后阶段拒绝了我。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问的人给出了模糊的答案,说我不适合。也许我听起来像个混蛋?老实说,如果这份道歉中的任何内容看起来像是会妨碍就业的人格缺陷,请告诉我。我只能说我开始感到害怕和痛苦。我在 TOC 上与 Oculus 进行了这次会面,希望这是我纠正错误的唯一机会。我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我将尽一切努力让自己受到关注——回想起来,我对此感到非常非常抱歉。
当然,当门终于打开,我走向 Oculus 展位时,里面空无一人。标牌没有立起来,免费的水瓶原封不动地放在桌子中间。说这是令人失望的情况是一种严重的轻描淡写。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在我的下一节课之前——我只是在 TOC 上踱步,希望 Oculus 能够出现。当然,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除了当天晚些时候的一个小插曲之外,Oculus VR 展位将保持无人值守。
最后,我放弃了,前往下一堂课。我被压垮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在大多数你想工作的科技公司中都拥有强大的校友基础,在此类活动之外还有一些简历渠道。但不是奥库鲁斯。 Oculus 对我来说太新了,无法真正认识任何可以推动简历的人。我知道如果我能踏进这扇门,他们就会感兴趣,对吧?我很想找人倾诉, 任何人 与连接。老实说,如果我没有想到接触 Oculus 的最佳机会就是在下一堂课上坐在我旁边,我可能会闲逛更长时间。
从理论上讲,有一个像乔治这样的朋友将是解决我这样的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他就像科技界的小名人,在硅谷拥有各种各样的人脉。他甚至认识 Oculus VR 的创始人 Palmer Luckey。但如果你真的认为这将是我的救赎,那你就不太了解乔治。
“什么,我只是要给帕尔默发电子邮件,然后说‘哟,我认识这个女孩,她很有才华,你应该雇用她’?不,我当然不会那样做。你不完全是约翰·卡马克。你觉得我应该做什么?”乔治说话带有浓重的高调泽西口音,我认为这放大了他所说的一切中有趣的居高临下的感觉。
“我……我不知道,让他把我的简历放在门下什么地方?我只是需要它来联系招聘人员,而不是首席执行官。”
“听着,如果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有一天晚上我会让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三个人去喝酒。但我不会突然给他发一封电子邮件来为你做担保。”
你知道吗?很公平。与公司创始人进行直接沟通并不是通过体面方式获得工作的好方法。不过,离得这么近还是很痛苦。我只是需要一个介入。不知何故,我会引起注意。
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开始将所发生的事情归咎于乔治。我尽量不因此而受到太大的侮辱。当然,《精英黑客获得进入大学体育馆的特权,暴露了职业公平安全中的漏洞》比我对失业问题的伤感咆哮来说是一个更好的经典,而且不需要几乎这种水平的阐述。事实上,是我对自己的无用和失望感到痛苦,说服乔治下课后和我一起参观 Oculus 展位。我们的一些同学后来声称他们在离开时听到乔治对我说,“想去 Oculus 展位并冒充一些招聘人员吗?”,但我坚持认为这没有意义,也不是事实。
当我们第二次到达TOC时,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曾经空荡荡的展位现在被穿着西装的孩子们围住了,所以我希望 Oculus 也能如此。当然,当我们到达时,那里没有人,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那里,因为没有人出现。我们在活动现场闲逛了几分钟,最后在 TOC 为数不多的空闲空间之一(Oculus VR 展位前)重新集合。
就在那时我看到了:桌子后面放着一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文件。 “嘿,看看这个!”我打电话给乔治。
“所以啊?”
“我不记得以前见过这堆东西。”
“不,我之前就看到过。这可能是所有想见识 Oculus 的孩子的简历……你认为招聘人员会回来接他们吗?
“诚实地?到最后他们就会被赶出去。”
该死。比不在管道中更糟糕的唯一事情是不知道自己不在管道中。老实说,当我看到这些简历时,我对其他孩子感到非常同情。和我一样,他们可能非常渴望与 Oculus 交谈,但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当他们看到空荡荡的摊位时,可能和我一样感到沮丧。现在连简历都看不到了!我希望我知道能为他们——为我们——做些什么。
就在那时,一个穿着西装的孩子走近摊位,握着乔治的手并做了自我介绍。在对他的教育、研究和职业抱负进行了 20 秒的独白之后,他给了我们一份简历。这太超现实了。
乔治措手不及。 “抱歉,我实际上并不为 Oculus VR 工作。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这份简历放在我身后的桌子上。这就是很多学生一直在做的事情。”
这是最尴尬的时刻。突然,西装小子所有的热情都消失了,他只是回头看着我们,不确定自己做错了什么。
“如果我把我的简历放在桌子上……它会传到 Oculus 吗?” “老实说我也不确定。”
犹豫了一下,他把简历放在一堆,然后就离开了。 “这真是他妈的悲剧”,就在我自己的一个微笑着的西装女孩迎接我之前,我咕哝了一句。她用我几乎听不清的声音问我们是否为 Oculus 工作。这一次,我尽快打断了她的话,给出了与乔治相同的解释。和最后一个人一样,她也很困惑。 “但是招聘人员最后还是会收到这些简历?”
“说实话,可能不会吧?但是,嘿,别相信我的话。”
犹豫了一下,她还是拖着脚步走开了,决定不丢下简历。
乔治和我用笑声打破了这种奇怪的感觉。它 是 有趣的是,老实说。但不仅仅是有趣,它也令人耳目一新。我整个早上都在担心我在这些招聘人员眼中是什么样子,他们会如何评价我。现在,我就是那个招聘人员,一切都显得那么低调。害怕 - 我的恐惧 – 我在学生的脸上看到似乎没有必要,他们的姿势如此......适得其反。就好像我可以看穿它,看穿他们的滔滔不绝,并且非常准确地知道谁值得花时间。我看到幕布后面的东西,感觉很棒。
我不想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听起来像是出于这种放纵或我“扮演上帝”的愿望。老实说,我们从未制定过任何模仿计划。
我只是对乔治说:“嘿。 ‘我们’认识 Oculus 的人,对吧?”
“当然。”
“如果这些简历无论如何都被扔进垃圾桶,也许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收集起来并发送给帕尔默或他推荐的人。”
乔治声称他从未同意过这件事,我想这可能是我编造的。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按照计划进行了。更多的学生过来询问我们是否为 Oculus 工作。每次,我们都会说“不”,并引导他们去看桌子上的一堆简历。不过,这一次我们也表示会尝试转发它们,因为我们知道 Oculus 的人可能会提供帮助。这些学生虽然还很困惑,但看上去比第一批学生高兴多了。他们递给我们简历,与我们握手,然后又漫步回到招聘会的内部。
现在我可以想象它的样子:两个看起来很怪异的人站在一个空荡荡的展位前,握手,说话,收集简历。那么,我就能理解为什么学生们已经开始在我们面前排起长队了。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说我们看起来像招聘人员确实有些牵强。标牌和水瓶仍然放在桌子上,没有人像招聘人员通常那样站在桌子后面,我们甚至没有戴名牌(在某个时候,乔治拿起一张写着“全职职位”的贴纸,然后把它贴在他的胸前,但这并不是一种模仿——他只是个白痴)。任何地方都没有 Oculus 标志——我们身上唯一的公司标志是 George 的 Google 运动衫和我的 Palantir 书包。据说,排长队是因为学生被误导了,但如果你问我,他们并不认为我们是招聘人员。和我一样,他们迫切希望与这家公司有任何接触,并且想要我们所提供的东西:任何接触 Oculus VR 的机会。
再说一次,我不想听起来像是我在为自己找借口。学生生活后来告诉我们,即使我们的模仿不是特别可信,我们仍然应该为“浪费学生时间”负责,这种冒犯虽然实际上并不违反规则,但对于规则来说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并且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时不时地引用会很有趣。这也可能是意图和结果不一致的地方之一,因为老实说,我不认为学生的时间被浪费了。我们与这些学生握手并给予了大约 20 秒的独白时间,然后无一例外地告诉他们我们不是为 Oculus VR 工作的。每次都会解释说我们计划转发简历,以及他们认为对招聘有帮助的任何注释(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接触,以免浪费他们进行真正的人际互动的机会)。
大多数学生似乎都能理解,并且仍然向我们提供了他们的简历,有时会犹豫地询问我们中的一个人,我们对这家公司及其发展轨迹可能了解多少。除了通过手机谷歌搜索 Oculus VR 收集到的研究之外,我没有太多要说的。另一方面,乔治很高兴地提出了他自己对 VR 未来的反乌托邦愿景,其中耳机已成为人类互动的必备品,图像被投射到你的视网膜上,为仿生眼睛以及很可能的奇点铺平了道路。如果当时有人认为乔治是一名真正的招聘人员,那么当我说我真的很抱歉时,我是真诚的。
你会认为这会很有趣。然而,尽管扮演学生们渴望找到的简历收集者的角色很高兴,但感觉有些不对劲。我们从来没有打算创造这样的场景。尽管坚持我们的原则并从需要的学生那里收集尽可能多的简历固然很好,但我们得到的关注很快就变得太多了,十分钟之内一切都结束了。我转向乔治,发现他也在想同样的事情。 “我们离开这里吧”,他说。我们从桌子上拿起简历,挤过人群,离开招聘会,就像我们来时一样秘密。
这就是很多人说我遇到麻烦的地方。还记得我说过的关于推迟事情的事吗?嗯,一开始我很难兑现将这些简历送到 Oculus 的承诺。我问乔治我们应该如何发送它们,最初,他说我们可以获取招聘办公室的联系信息并传真给它们。然而,当天晚些时候,他表达了怀疑。首先,他声称我们没有遇到任何他认为有资格在 Oculus 工作的人(他的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认真看过任何简历)。最后,他承认他对与帕尔默交谈感到紧张。他非常尊重这个人,如果必须向他解释情况会很“尴尬”。好的。由于没有立即制定 B 计划,我决定推迟它并让它静置,直到四天后我从 Nvidia 现场回来。
我现在被告知,到那时,TOC 政府内部已经敲响了警钟。回来后,我仍然不知道这一切,我找到了一位我信任的 SCS 教授,问他对简历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他说我可以把它们给他,他会想出如何处理它们。
再说一次,我有一个推迟事情的不幸习惯。我花了两天时间才拿回简历,在此期间,向学生和非学生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警告称,两名身份不明、无关联的嫌疑人冒充招聘人员进入了 TOC,随后带着招聘人员离开了。一堆学生信息。虽然这封电子邮件是发给大部分学生、校友网络和行业合作伙伴的,但实际上并不是发给我的。乔治和我最终通过朋友得知了这封电子邮件,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其他方不仅知道我们的行为,而且还对此感到震惊,因此有必要通知大学和行业我们的行为造成的威胁。就在这时,我终于把简历交给了我们的教授,确保TOC的相关人员看到了这些简历,然后我想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我感到非常非常抱歉的行为的开始。显然,简历的归还以及我们的教授关于我们是本科生而不是恐怖分子的承诺促使我们进行了相当大的内部和外部调查,以确定我们的身份。我听说匹兹堡警察局介入了。我听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侦探被派去调查这个案子来追踪我们。首先,我不知道 CMU 有侦探!他们整天做什么?乔治发现了一个案件,侦探们被叫去调查一名学生,该学生带着三个女孩进入他的宿舍“帮助组装家具”。归根结底,我认为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侦探们很高兴能解决一个真正的谜团。我不会为此道歉。
在这一点上,如果不是因为以下两件事,我们会很高兴地放弃自己并阻止这项调查的最终规模:
首先,关于乔治:乔治对警察的话题非常非常敏感。乔治被索尼起诉,因一些令人讨厌的持有大麻指控而上法庭,再加上一般的反独裁性格特征,乔治对警察的印象并不好。事实上,我什至可以说他害怕他们。在我们听说正在进行调查的第一天,我收到了乔治的一封电子邮件文章,内容是在审讯室里应该说什么或不应该说什么,他正在与他的律师团队进行初步对话。你需要明白,仅仅告诉乔治不会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是不够的。对于乔治来说,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会抓住你最微小的违规行为,并将其作为一个机会来搞砸你。
其次,我想我只是觉得侦探们会找到我们。老实说,我们并不是想隐藏自己,在一个只有 400 人左右的学校里,询问几个 SCS 学生并发现我们的身份并不难。而且,乔治还是整个大学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当我们得知他们有我们的照片时,有人认出我们似乎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们等待。我们 推迟 做任何事情。
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得知自己正在被搜查的消息开始对乔治产生了影响。他没有上课,而是给我发电子邮件规划我们的策略或与他的律师的下一次会议。当我终于再次见到他时,他看起来很震惊。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想我需要让我的律师一起自首。”
“好吧,等一下。你仍然认识 Oculus 的首席执行官。你不能联系他,让他告诉 TOC 的人他不在乎吗?我的意思是,他可能不会,对吧?”
乔治想了想。 “不。就像我说的,我真的不想因为这种愚蠢的事情来打扰他。就像,我真的要请求一家公司的创始人保释我,让我摆脱这基本上相当于愚蠢的大学恶作剧?”
“我们还要做什么?”
最终,乔治屈服了,给帕尔默·拉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几乎立即做出了回应——他听说了这件事,并认为这很搞笑。最后他只说了一句:“我来处理”。
“这意味着什么?” 我问。
“我不知道,我们也不会知道,因为我不会再给他发电子邮件了。”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帕尔默的消息了。也许他也把事情推迟了。无论如何,这对乔治来说太长了。几天后,他早上 6 点给我打电话,惊慌失措。 “我不能再忍受这个了。压力太大了。我要自首”。
我不是来见证乔治挺身而出的。据乔治说,他走进 CIT,愉快地向 TOC 的组织者打招呼,并耐心而成熟地倾听,因为他因我们造成的所有损害而受到残酷的惩罚。据政府称,乔治粗鲁且好斗,他的挺身而出只会让关系变得更糟。我从我们的教授那里听到了这一切,他也鼓励我挺身而出,但也许要尝试少一点“无礼”。
因此,这次推迟了几天后,我起草了第一封道歉信,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对我的行为给政府造成的任何损害表示遗憾。我把它发给了我的教授,他又把它转发给了合适的人。我希望这能为这些人提供一个了结,为他们提供了解我们的行为和动机所需的信息,并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绝不会对学生或 TOC 构成威胁。当我说我对我们引起的反应感到难过时,我是真诚的,现在我想自愿提供这些信息,希望能帮助每个人最终高枕无忧。
当然,乔治和我还不明白,在 TOC 的组织者再次感到安全之前,我们需要更多的悔改。
几天后,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主题为:“面试”。对于秋季学期的 CS 专业来说,没什么不寻常的,尽管我不知道这次面试的对象是谁。最后,当最后几行指定了我们采访的地点时——Quiznos 和 Razzy Fresh 之间的克雷格街(Craig St)——我突然明白了:那就是警察局所在的地方——这将是一次与警察的“采访”!
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样,乔治对此一无所知。 “我不可能和警察说话!他们的全部目标就是用你自己的证词吊死你!该死的,我真的不想为此请律师!”我们的教授本人也有法律经验,对此表示同意。警察是个坏消息,与警察的任何互动都意味着要聘请昂贵的律师。所以我回复警察,说我们拒绝与任何警察交谈,这就是我们被引导到学生生活办公室参加纪律听证会的方式。
到现在为止,乔治真的开始失去理智了。他六周前就不再上课了,并计划再次退学。 “我一直在去俄亥俄州公路旅行并收听硬核历史播客,”他告诉我。 “这就是让生活变得有价值的原因。”他说,虽然他计划退学是出于调查的动机,但我不应该认为这是我的错。 “如果我从远处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你敢打赌我会尽可能远离这所噩梦大学。”
学生生活的纪律调查步骤如下:
第一步:他们会收集我、乔治和任何愿意站出来描述他们与我们一起经历的学生的证词。
第 2 步:他们会让我和乔治参加一次会议,会上他们会列出调查结果以及我们被认为违反了卡内基梅隆大学学生行为手册中的哪些规则。
第三步:一旦我们所有人都就违规行为达成一致,他们就会给予惩罚。
随着调查的进行,乔治和我会仔细阅读卡内基梅隆大学学生行为手册,试图找出我们的违规行为。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例如禁用或更改同学的生命支持设备,或者逆向工程和利用第三方软件的违规行为。然而,最终我们还是很难找到我们在这起事件中犯下的罪行。当然,没有做过调查的人可能会说“冒充另一个人”,但这似乎很弱,因为我们已经向我们遇到的每个人表明了我们是谁,即使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并不是试图“冒充”任何特定的人。
最后,我们谈到了最后的违规行为:“卡内基梅隆大学学生的不当行为”。 “那有什么意思?”我问乔治。
“这就像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以防他们想要添加一些东西。我认为他们不能 只是 用那个来打击我们。这似乎太模糊了。我的意思是,你必须真正违反某些规定才算违反,对吧?”
当然,我们现在明白我们当时是多么被误导了。当询问为什么我们被指控的任何事情实际上都不符合真正的规则时,我们被告知“我们 [CMU] 认为我们不需要一个规则,因为我们认为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个观点与乔治和我自己在计算机安全和系统软件方面的背景产生了共鸣。
《学生生活》一致认为,虽然乍一看这起事件看起来像是冒充他人,但它不符合“冒充他人”的标准,因为他们采访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他们感到被误导了。事实上,Student Life 和我最终在很多事情上达成了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并没有感到受伤,Oculus VR 也没有,后来他们与大学取得了联系并发表了声明。
然而,《学生生活》也认为,我们仍然应该因犯下“卡内基梅隆大学学生的不当行为”而受到惩罚,原因如下:
1. 浪费学生时间
2. 回复简历和纠正情况的时间过长
3. 引起 TOC 的反应,最终让他们感到尴尬,暴露了冒充行为是多么容易发生,并给他们的名字带来了“污点”。
我解释说,我很困惑,我们怎么会因为站在展位前收集学生向我们提供的包含完整信息的简历而感到内疚,特别是因为事实是 不 政策的阻止是 TOC 最初感到“受挫”的原因。乔治最近听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硬核历史播客,他将这种情况与斐迪南大公被刺杀进行了比较,并一直坚称,除非他明白“我们要向谁支付赔偿”,否则他不会满意。我知道这让我们的面试官感到惊讶,用他们的话说,“令人难忘”。我不会为此道歉。
最终,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为“不当行为”提供 20 小时的社区服务,写一篇反思性文章,也许还需要道歉。当然,这只是针对我的,因为乔治现在已经辍学并搬到加利福尼亚去追求更伟大、更奇怪的事情。
或者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我宣判三周后,他回来了,并安排了与学生生活的另一次会面。 “不再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对吧?”我恳求道。
“不可能,”他带着令人担忧的笑容说道。 “我这次一直在读成吉思汗。”
我确信这次会议对我来说意味着死亡,然而几天后,我又收到了来自学生生活的电子邮件。对我的所有指控均被撤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现在我所要做的就是向他们道歉。电子邮件称,这不是一项要求,但由于我们声称表达了真正的遗憾,因此我们为受影响的各方真诚道歉似乎才是公平的。
同样,我没有被告知这些受影响的各方是谁,但通过排除过程,我的猜测是 TOC 的组织者,那些因我们的行为而“受损”的人。我可以理解他们的观点:也许我的行为和由此产生的反应永远损害了与 Oculus 的关系,因为我们暴露了可能会在他们的事件中产生不信任的“漏洞”。当然,如果没有道歉,这些人会感到受到威胁和不安全,这是有道理的。
请允许我让这些人放心。这个月初,我做到了——我终于踏入了 Oculus VR 的大门!我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一位名叫罗布的工程师,原来他在那里工作,我们开始了交谈。我设法把我的简历交给了他,幸运的是,他们第二天就对新员工进行了审查!我被列入名单,他们看了我的简历,正如我想象的那样,他们也认为我很合适。提交申请后不到一周,我就收到了一份offer。
几天后,真正的 Oculus 招聘人员找到了我。他们听说了我的新提议,当然也了解去年秋天 TOC 的所有业务。幸运的是,两周后他们就来到了 EOC。他们想知道我现在是 Oculus 的正式员工,是否有兴趣作为官方招聘人员参加这次活动。老实说,我很高兴。这么快就受到公司的欢迎,并为上学期感到非常失望的学生提供真正的服务,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们开玩笑说,作为 Oculus 的高级招聘人员,我必须向他们展示该怎么做——“帮助我们找出这些学生中哪些是合法的。”
经过几个月又几个月的失业思考,不得不向数十个指责的面孔解释自己,我终于站在了另一边。我看到像我和乔治这样神经质的尝试者在我的展位前排队,递给我他们的简历,并给我一些紧张的演讲,告诉我为什么我,Oculus VR,应该雇用他们。有些人足够优秀,他们只需要给我他们的简历即可。通常,那些有大而花哨的独白的人都太努力了,我只需要看一眼他们的工作经历和一些简短的问题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如果说我从这整个经历中学到了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不要那么努力地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目光明亮、真诚且值得,世界最终会改变它所需要的方式,以确保事情最终顺利进行。
最后,TOC代表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对我或我的新公司做出太严厉的评价。去年秋天,我们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还年轻,紧张,渴望给人留下好印象。不知怎的,我们俩最终都被误解了。不过,到了春天,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期待在未来的 TOC 和 EOC 中与您合作。至少,我确实如此。
当然,如果您想从马口中得到它,我鼓励您直接将您的担忧发送给我,我一定会尽快将它们转发给我的人帕尔默。我听说我们很快就要聚在一起喝酒了。